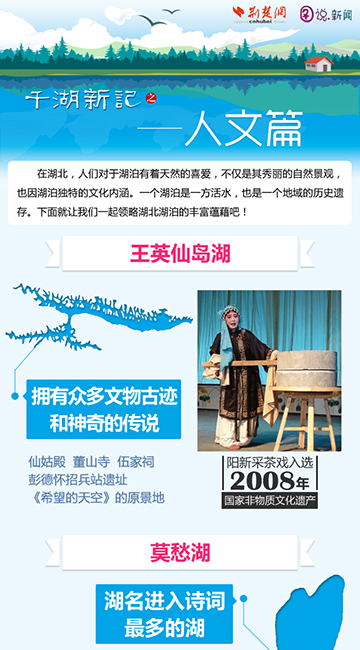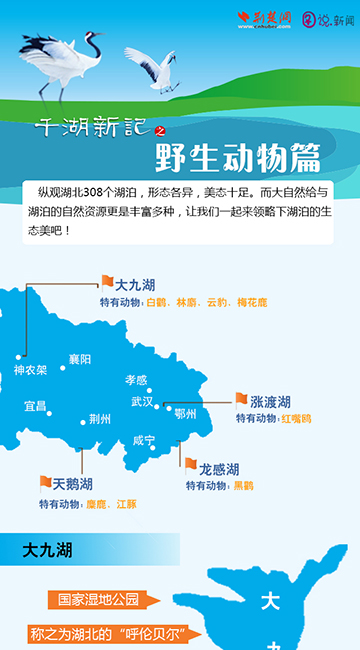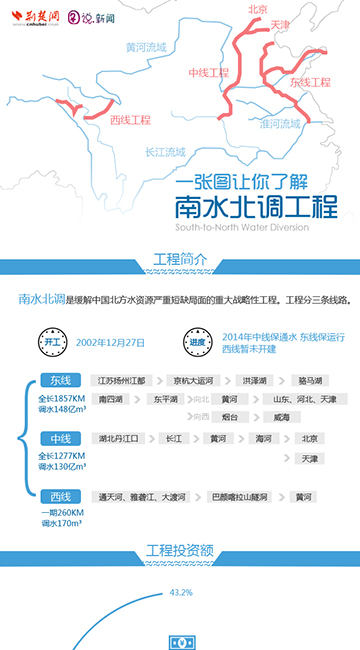且听他们说家园
普安村傍湖而居。
村里的空地铺上了网纱,晒着莲子。种植香莲,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。
7名妇女正在湖边的树荫下收莲子。许多刚从田里采摘的老莲蓬已呈乌黑色,用竹片削成的“敲子”一叉,再在砖块上敲几下,莲子就从莲房里掉出来。她们熟练地重复着,一会儿功夫,莲子便堆得小山高,一上午能收50公斤左右。这些老莲子,以后会加工成干白莲。
“人工太贵,所以左邻右舍互相帮忙。”35岁的黄建华头顶草帽,身穿长袖,手上还戴着毛线手套。她一边敲打着莲蓬,一边告诉我们,家里既种香莲也养鱼,相比之下,养鱼成本较大,还有一定风险,所以她觉得种香莲不错。但今年收成差一点。
妇女们在一旁插话:“遇上干旱,香莲减产了。”“我们农村人,不就盼着阳光、雨露?”
香莲、荷叶茶、鲜鱼……对勤劳的村民们来说,悠悠湖水,承载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许。
其实,对于在生态与效益之间选择,不少村民的心情也有些复杂。
“以前水质好很多,现在效益好很多。”57岁的宋来堰这样描述记忆里沧湖的变化。他曾是国有渔场的守湖职工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渔场将粗养湖汊改造为精养鱼池,承包到人。从那时起,家里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变化。目前,他家有19亩鱼池、4亩多香莲,再加上其他一些活计,一年收入大概4万多元。
58岁的余存伟过去也是渔场职工,每月工资三四十元。1985年前后,精养鱼池分到户,一个劳动力分10亩池子。日子越来越有奔头,但他心里有些怅然:“30年前,沧湖满眼港汊、芦苇、野莲蓬,到处是野鸭、獐鸡,生态好得很。当时养鱼没用过肥。”
荷间又见挖藕人
初秋的日头依然火辣。勤劳的挖藕人,在湖面投下剪影。他们有欢喜,有叹息,更有长长的期盼。
中湖之畔,一筐筐刚挖出来的鲜藕堆放在马路边,安徽老板李忠龙安排工人们过秤、装车。他和4个搭档一起承包了中湖的3000亩水面,用来种莲藕,今年高温少雨,反而有了好收成。每天,这里至少要拉走三卡车鲜藕,运往北京、广东、四川等地。
远眺,荷叶摇曳,掩映着一群挖藕人的忙碌身影,腰部以下都浸泡在泥水里。他们大多来自河南、安徽、湖南等地,7月底已开始在此挖藕,将持续至过年前。对他们来说,比起隆冬泡在刺骨的冰水里,顶着烈日劳作已是最好的时节。
挖藕人早上7点开工,中午12点上岸吃饭,短暂歇息后,继续下水。挖一公斤藕,报酬约在8毛钱左右,一天下来能挣几百元。
傍晚时分,余晖向湖面撒下一把把碎金。荷叶深处,一艘艘载满鲜藕的小船衔尾而出——挖藕人收工了!
40岁的石贵马和妻子奉树香收工后,在湖边搓洗着沾满淤泥的衣服。尽管疲累,黝黑的面容上仍流露着笑意。这一天,夫妻俩一共挖了1300公斤藕,可以拿到一千元工钱。他们来自湖南永州,柳宗元笔下的捕蛇人后代,如今在这里挖藕,要一直挖到冬天。
石贵马还在和同行们唠嗑,奉树香先上岸了。她一身湿漉漉的,朝着不远处的简易工棚走去,语调里却透着几分轻快:“回去煮饭喽!”
“这里产的藕,质量好。”50岁的吴再光来自湖南益阳。身子还泡在湖水里,便点燃了一支烟,享受辛劳一天后的闲暇时光。他每天能挣几百元,但平时只抽4元一包的香烟。
吴再光15岁开始挖藕,已经挖了30多年。聊到这,他不禁叹口气:“很多晚上睡不着,风湿疼啊,也想几岁的孙子。”他随即开朗地笑笑,说“再苦,我也还是会挖下去。”
(作者: 编辑:ADMIN)
 闁倸鍙曠純鎴濈暔婢讹拷 42010602000206閸欙拷
闁倸鍙曠純鎴濈暔婢讹拷 42010602000206閸欙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