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
在缉毒类型剧《扫毒风暴》中,段奕宏饰演卧底警察林强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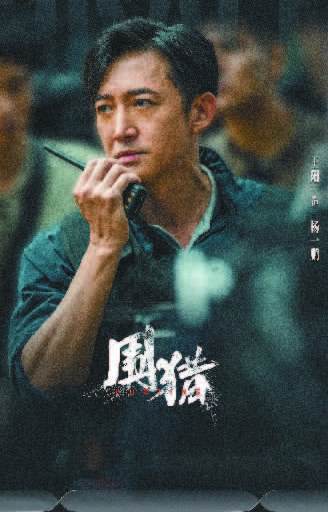
《围猎》中,王阳饰演卧底警察杨一鹏
《围猎》开播之时,我既期待又好奇。我想知道,在“缉毒”这个相对狭窄却一直很受欢迎的类型中,《围猎》的坐标大概在什么位置上。我更想知道,相对于前一阵刚刚结束热播期的《扫毒风暴》(2024年2月开机,33集),早在2023年就开机、中型体量(24集)的《围猎》,还有没有可能翻新故事的讲法。
答案有点五味杂陈。
无论是从数据、影响力还是成片质量来看,《围猎》都属于那种能站上及格线但一伸手就摸到天花板的作品——下限不算太低,上限确实不高。不过,我一边看,一边还是觉得有话可说:因为通过这部剧,其实你能看到属于这个类型的几个共性问题。
也许可以这样说:无论是《扫毒风暴》,还是《围猎》,都是这个特殊剧种的横断面。透过它们,缉毒类型剧的发展脉络、前世今生,这个类型的“爽点”与“痛点”,都有迹可循。
一
缉毒题材其实有天然优势。
在“公检法”大类中,缉毒是非常特殊的警种。缉毒警隐姓埋名,刀头舔血,与亡命之徒持久博弈,这样的故事天然带有强烈的神秘性、感官刺激、内在张力以及触角能伸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延展性,是生长好故事的优良土壤。
不过这个类型实在太特殊了,特殊到有时候也会带来叙事的双刃剑,给影像表现设置高难度。它往往不像刑事案那样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案发现场,从一具尸体或者一个爆炸现场出发,抽丝剥茧地依靠逻辑推理查找真凶;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“猫鼠游戏”,黑白泾渭分明,明处的警察与暗处的罪犯隔着真相的帘幕互相牵制。
在缉毒剧中,“猫”是必须孤胆深入“鼠”窝的——鼠窝的犯罪链条既复杂又漫长,既琐碎又危险,从境外毒枭到各种运输、销售的中间环节,上游直抵制毒师,下游渗透到街头巷尾的毒品受害者。
在这样的设定下,缉毒警的生活和工作长期处在凶险、恶劣且琐碎的环境里。把这些来源于现实的细节掰碎了揉进虚构故事以后,也许会给叙事框架和剪辑思路带来不少困扰。实话实说,在信息分配的问题上,《扫毒风暴》和《围猎》尽管采用不同的方式,但都没有解决好。
《扫毒风暴》的体量更大,人物更多,技术上也更花哨,所以场面上会显得更乱一点。我不能理解的是编导太喜欢在时间线上来回横跳,再加上过于频繁地使用手持摄像机,未免对观众的耐受度要求太高。第二集,林强峰与卢少骅相遇,一顿切磋,侧面的机位晃晃悠悠来回怼着脸儿正反打,似乎要把并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词儿硬晃出信息量来,辅之以幽暗荧光绿配色,心律不齐型配乐,一看一个不吱声。
好在,开播之后不久,片方就重剪了开头几集,又使用技术手段稳定了镜头,总算是及时拉回了口碑。
《围猎》在信息分配上同样顾此失彼,始终在一大把线头之间疲于奔命,剪刀明明忙得气喘吁吁,但观众还是看得一头雾水——重点不清晰,节奏还提不起来。依我看,如今的影视工作者,恐怕应该回过头来,重温一点传统线性叙事的精髓。尤其是在剧作开篇的黄金时间段里,应该让观众跟着主要人物的视角稳定而快速地多走两段,在人物与观众之间建立有效的情感联结。演员需要信念感,其实观众也需要——你得给他们跟下去的理由。
不过,在一些关键信息或者重场戏的处理上,《扫毒风暴》还是显示出比《围猎》高一个台阶的虚构能力。比如,同样是制毒,卢少骅的实验室场景就比牟森的海滩帐篷更有现实感;同样有抓内鬼环节,《围猎》里的内鬼硬是一眼就猜得出来,潦草得宛若过场;同样是境外毒枭两代人的家变,《扫毒风暴》就是能拍得更跌宕,更耐嚼,也更有想象力。
二
国外的“涉毒”题材作品,从《绝命毒师》到《毒枭》,几乎都把重心落在毒贩身上,以细腻扎实的虚构功底,刻画极端环境中的极端性格,将神秘、复杂、阴鸷的张力拉满。
也许正是因为上述作品的影响过于深远,所以,一旦到了国产片的特殊语境下,缉毒剧编导对于正反派人物的塑造,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微妙的“左右为难”。
2024年出过一部豆瓣评分仅有4.3、播放量却相当可观的缉毒剧《猎冰》,其实大体上沿袭的是海外的经验,完全聚焦在传奇制毒师黄宗伟身上——但这样的沿袭,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已。
《猎冰》制作上的粗糙与捉襟见肘,跟女主角姚安娜(警察)的演技一样令人尴尬,但这部剧的播放赶上了最好的时机。彼时男主角张颂文身上还满载着《狂飙》热潮后留下的余温,刚好能用一己之力,把这一锅《猎冰》的杂和菜,炖热,上桌,甚至还能听到有人喝彩——虽然说不清其中有多少是冲着女主角喊的倒彩。
平心而论,在大部分环节,《扫毒风暴》和《围猎》都比《猎冰》做得更讲究。两部剧的编导,也都意识到要尽可能在正反两端保持均衡。
《扫毒风暴》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将“双雄博弈”的主线贯彻始终,双男主(段奕宏,秦昊)的配置确实也当得起“双雄”的分量。站在“正方”的角度看,缉毒警要真正捣毁毒贩窝点,切断这条残忍凶险、盘根错节的生态链,往往需要有人舍生忘死,长时间潜伏在其中。因此,情报工作是缉毒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从警方视角切入的故事,完全具备与“谍战”套路嫁接的可能。
然而,《扫毒风暴》并没有把林强峰(段奕宏)的故事讲好。在林强峰当卧底的那些剧情中,这个人物几乎一直困在混乱的时间线里,视角与行为逻辑犹疑不定。在这个故事里,我们能看到多年卧底生涯与战友的牺牲,给林强峰带来多大的心理创伤。而观众最关心的部分——他究竟怎样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潜伏中获得情报、打开局面,反而被处理得支离破碎;与反派卢少骅(秦昊)清晰跌宕、层次分明的“堕落线”相比,林强峰的“成长线”反而是破碎的,模糊的,摇摆不定的。
很多人都说段奕宏在这个剧里的表演用力过猛,我也部分同意。但我想,如果认真讨论这个问题,首先还是得考虑一下,剧作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是不是给演员——尤其是那些有想法、有创作欲望的演员——预制了“表演陷阱”?
三
在《围猎》里饰演卧底(特情)警探杨一鹏的王阳,面对的也许是另一重困境。
为了替牺牲的伍队报仇,为了不辱使命,杨一鹏决心“沉下去”,蜕变成邋遢油腻、混迹于市井的卡车司机镇哥。穿劣质花衬衫,踩趿拉鞋,粘胡须,戴假肚腩,混迹底层,打架蹦迪,撕掉都市精英的形象标签,甚至掩藏漂亮的台词功底,在全剧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都操着半咸不淡的南方沿海口音——凡此种种,对一个成熟的、可塑性强的演员,都不是问题。事实上,最初被吸引入场的观众,也有相当数量是被王阳巨大的形象反差,勾起了好奇心。
问题是,演员完全准备好了,编导有没有?剧本有没有给如此富有诚意的造型和表演状态,赋予足够的台词、动作、事件和情境?
镇哥与马仔叔在码头上不打不相识,进而通过他结识毒品转运渠道上的金牙万。接下来,杨一鹏(镇哥)的行为逻辑,就应该是顺着这个突破口深入贩毒生态链,一步步抵达生态链的核心,利用其中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,并且在种种千钧一发中化险为夷,在压迫式的极端环境中体悟人性张力。这是缉毒类型片的爽点,也是观众合情合理的期待。
但不知道为什么,编导似乎重蹈了《扫毒风暴》的覆辙,将本来完全能够一以贯之的视角随意转换。在大部分时间里,编导似乎并没有给镇哥认真安排顺藤摸瓜的任务——藤明明在身边,瓜明明在前方,但镇哥却常常突然停下脚步,时而回到外围底层,跟商贩聊天摸排零星线索,时而用其他警官的名义质询证人(人物无视警队纪律,编剧也违背了基本常识),时而又冲到游艇上,去干一线海警才会执行的追逃任务,不顾这样做完全可能暴露身份,完全可能在离目标尚远(他追的船里并没有他的头号仇人牟森)时,就让他的卧底行动前功尽弃。
自始至终,演员的状态是饱满的,表达是准确的,但编剧的随心所欲,让人看得骨鲠在喉,总想追问一句:
“整整三年的卧底,以杨一鹏的能力,为什么始终在边缘地带兜圈子?究竟是警察探案的效率不高,还是编剧叙事的效率太低?”
四
那么,我们不妨再追问一句,当杨一鹏被迫在原地转圈的时候,编导把叙事重心挪到了哪里?
挪到了少男少女的情感纠葛中。
一个是毒贩阵营里的迷惘少年多仔,一个是牺牲警察的女儿之安。他们之间的感情戏,从《围猎》开局一直贯穿到最后。在此期间,为了让他们始终纠缠在一起,编导安排了纯情的巧合型设定(同一个生日,古典得就像狄更斯的小说),浪漫的网恋(大量篇幅都用在不利于影像表达的网络聊天上,结尾让少年在网游中“重生”),以及身处两个阵营的煎熬与拉扯——一时间,这样的情节,这样的台词,让我恍若回到了千禧年代的《永不瞑目》(2000)和《玉观音》(2003)。
然而,把缉毒剧与青春苦情偶像剧拌在一起,炒成一盘融合菜,那是二十多年前海岩精心打造的时代乌托邦。在我看来,把这样的框架搬到2025年,再加上对网络游戏的一知半解的呈现,不仅有点过时,而且,对于叙事效果而言,损失大于收益。一方面,叠加的巧合折损了故事的逻辑,割裂了缉毒主线;另一方面,言情风格的强行融入,大大拖慢了类型剧的节奏——后者显然更致命一点。
自始至终,节奏一直是《围猎》最大的问题。如果这个故事从第7集讲起,并且始终保持7、8、11、12乃至16集以后(尤其是大结局)的节奏,那么,即便情节仍然存在很多破绽,至少可以在节奏上抓住类型剧那一批最忠实的观众。
无独有偶,其实《扫毒风暴》里的感情戏,或者“准感情戏”,也总是给人一种“滑到哪里算哪里”的注水感。卢少骅对三个老婆究竟有没有一点真情?林强峰与摇滚歌手王奇(于文文)之间,那大段大段的“唱歌+哑谜+劈情操”的对手戏,到底是什么意思?编导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扔给观众,然后扭头就跑。好在这些云山雾罩的情感线,在《扫毒风暴》里占比要明显小于《围猎》,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。
五
当然,如果抛开类型剧的规则,故事是不是还存在另一种讲法?当然有,而且也有成功的案例。
去年的《我是刑警》就全程采用近乎纪录片的纪实风格,《围猎》在前期宣传时,也曾强调过这部剧脱胎于真实案例,因而具有比一般类型剧更深刻的社会性。
然而,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,就能看出《围猎》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。
第六集,两个警察审马仔叔,台词里所有的内容都是功能性的。杨皓宇演得很松弛,努力将其实并不大的信息量,用生活化的语言撑满五分钟。但不管他怎么努力,剧本提供的规定情境就这么些,除了交代情节,并没有多余的用处。乏力的叙述,让这五分钟显得很漫长也很寡淡。
我们可以用《我是刑警》的任何一段庭审戏来加以对照——不管是审白玲的,还是审张克寒的。人物的性格与经历,时代的细微变迁,那些在冰山之下奔涌的厚重的情感,既逼真得仿佛就发生在身边,又充满内在的、古典的戏剧张力。在这些戏里,你仔细听,人物絮絮叨叨、颠三倒四的叙述里折叠着内容——不同的人能听出不同的层次来。当我们感叹于和伟、富大龙或者马苏的表演功力时,不要忘记——剧本中充沛的、真正扎根于现实的细节,给了演员最充分的信念感,这是所有“演技”得以充分施展的前提。
所谓的社会性也好,纪实风格也罢,最终依托的都是故事本身的成色,是叙事技术对现实的高度提炼。这并不是单靠风格化的影调,手持摄像机晃晃悠悠地一镜到底,或者全体演员学会陌生的、充满喜感的口音,就可以实现的——无论是《扫毒风暴》,还是《围猎》,也许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(黄昱宁)
Copyright © 2001-2026 湖北荆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
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证 4212025003 -
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鄂B2-20231273 -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(鄂)字第00011号
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1706144 -
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(鄂)字3号 -
营业执照
鄂ICP备 13000573号-1 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206号
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206号
版权为 荆楚网 www.cnhubei.com 所有 未经同意不得复制或镜像